沈绰这一巴掌,卯足了全身的劲儿,披风下的满身璎珞,哗啦啦,叮咚作响。重生后的这一会儿功夫,她已经十分克制,努力做个端庄贤良的大家闺秀!可这姐妹三个,一而再,再而...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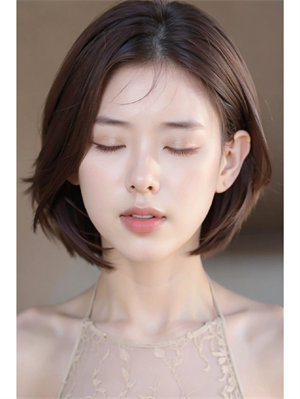
沈绰这一巴掌,卯足了全身的劲儿,披风下的满身璎珞,哗啦啦,叮咚作响。
重生后的这一会儿功夫,她已经十分克制,努力做个端庄贤良的大家闺秀!
可这姐妹三个,一而再,再而三地得寸进尺,她强压着的满身暴脾气早已忍无可忍!
“啊!”
沈相思花儿一样的人,当场被掀翻在地,挨揍的那半张脸,登时肿了起来,不但映出五指印子,还因着着沈绰手掌上的璎珞链子硌得,起了数道错落的红凛子,乍一看去,如被人用刀划了个大花脸,煞是骇人!
好狠一巴掌!
在场所有人,又是倒抽一口凉气,兰公公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脸,不知道为什么,有几分庆幸。
他们怎知,扇耳光这种事,沈绰当国师的十年,已经练得炉火纯青,可以打人噼啪作响,自己却手掌不疼,而且想要巴掌印就有巴掌印,若想没有,也能打掉了牙齿,旁人都看不出半点痕迹。
“沈绰,你竟敢动手打人,莫不是做贼心虚?”沈胭脂见此情景,嘴上还要逞强,心中却是骇然,脚下往后退了一步。
沈绰见一巴掌居然没镇住场子,心中更加不悦,二话没说,回手抄起身侧小几上供着桃花枝的细颈白瓷花瓶,咔嚓一声敲在桌角,瓷瓶哗啦啦碎了一地。
她几步将沈胭脂逼到墙角,一手掐住她的脖颈,另一只手掐着半截花瓶,将参差狰狞的断口指向花容失色的脸,“我沈绰如何,永远都轮不到你们几个说三道四!记好了,从今往后,谁再敢在我背后动半点非分之想,我就让她求仁得仁,此生再也没地方抹胭脂!”
这一声,任是傻子,也听得出来,不是威胁,而是警告!
沈绰的脸,未施粉黛,纵是国色,也苍白而阴郁,双眼仿佛无底深渊,直通地狱,她将头微微一偏,鸦羽样的睫毛,缓缓轻掀,嗓音更沉,“懂?”
“懂……懂了……”
沈胭脂吓得连眼珠儿都不敢乱动一下,本想要嚎啕撒泼,可嗓子眼儿被因威压而来的恐惧堵着,哭声就又被噎在半路,强行憋了回去。
“还有哪个对我的脖子感兴趣,站出来!”
啪!沈绰甩手将手中半截瓶子摔了个粉碎,目光将在场众人全部扫视一圈。
门口那些看热闹的,就立刻纷纷将目光移向别处,再没人敢与之对视。
这次,沈绰离开时,围观的人群自动让开了一条更宽的路来,任由她跨过门槛,迈入冰凉如水的夜色之中。
身后,是沈碧池绝望的嚎哭,还有沈胭脂姐妹恨毒了的目光。
前世,在里面瘫坐哀嚎的,是她沈绰,除了小薰,又有谁曾经给过她半点怜悯?
就连从昆明宫闻讯赶来的姑姑和爹娘,也是一脸的厌弃和不耐。
他们怪她没有城府,没有心机,不识大体,不顾大局,出了这种事,非但不懂得掩盖不堪,还要闹得人尽皆知!
她不但将沈家的脸面丢了个精光,还给皇上惹来了无数麻烦!
她不是受尽惊惧和屈辱,应该被家人好好呵护安慰的女儿!
她是那罪该万死之人!!!
沈绰脚下每踏出一步,杀机仿佛都能开出血色的莲花。
可这一身的戾气,乍一翻滚,很快又被另一个念头轻轻盖过。
这辈子努力做个好人,再也不给他丢脸,再也不惹他生气……
想到墨重雪,沈绰绷紧的嘴角,重新挂上一抹柔和上牵。
过了今晚,就去找他,跪在他门前,娇滴滴地唤一声师父,这乖乖徒儿,他不要也得要!
——
与此同时,在皇宫的另一处角落,一间不起眼的房间,门外上下前后,布满了暗卫,如一张密不透风的金钟罩,将屋子里面的人,牢牢护了起来。
房中,频频传出男人深陷昏迷之中的隐忍闷哼。
床榻上,如雪银发,瀑布一样铺落到地面,男人衣衫半掩,面如金纸,两眼紧闭,难掩天下无俦的盛世风华。
他的手中,紧紧攥着一把小小的银刀,只有掌心大小,却因用力过猛,两侧刀刃深深嵌入血肉中,鲜血顺着指缝溢出,染了床边一片殷红。
床边凳上,坐着个青年,身穿青色长袍,正小心翼翼地转动男人头顶几处要害的银针。
直到最后一根银针拔出,男人长而整齐的睫毛,才终于激烈地簇动了几下,之后,唰地掀起。
一双瞪大了眼睛,空茫地望着帐顶,通身绷直僵挺,如一具华美的死尸。
那是一双极其漂亮的凤眸,眼尾轻轻上扬,生了完美的弧度,还带了些许薄红。
“主上,回神!”耳畔,青衣男子一声轻唤。
男人的睫毛忽而微颤,之后,吐出长长一息,双瞳逐渐凝聚,之后如劫后余生,光芒大盛,是前所未有的澄明!
冲破生关死劫,化境已成!
“青檀,辛苦了。”他坐起身子,将如水样的黑色丝袍拢起。
嗓子有些黯哑,却是昆山玉碎,闻之入骨三分。
“恭贺主上,更上一层楼!”
余青檀欣喜,扶男人起身,伺候更衣,“属下已经派人查过了,今晚的饮食用器都没有问题,唯一可疑的,便是之前冲撞了您的那个酒醉的侍卫,身上曾被人用了见不得人的药粉,不想歪打正着,反而激活了您的血脉,这才能一蹴而就,强行冲过了压制已久的关隘!”
“呵,哪儿来的那么多巧合,想必是南诏人的安分日子过腻了。”男人摊开手掌,长眉微凝,眼帘忽闪了一下,阴影掠过,危险如斯,“尸体可处置好了?”
他的掌心里,安然躺着一把染满鲜血的百宝裙刀,做工奇巧,不该是小小的南诏国所出之物。
“这个……”提及此事,余青檀神色艰难,扑通一声,屈膝跪下,“主上恕罪,是属下等失职,那女子非但没死,反而大肆哭闹,属下派人折返时,已有禁卫军给压了下去。”
“哦?”男人的一侧眉梢,陡然轻扬。
那样都可以不死,还有劲儿兴风作浪!
余青檀匍匐在地,牙关紧绷,“主上息怒,属下这就亲手善后,将所有人知情之人全部灭口,将功补过!”
“不必了。”男人沉沉一声,将掌中裙刀重新攥紧,全不顾掌心的伤
![]()
口还在淌血,“光明正大地找出来,带回不夜京,慢慢处置。”
那女人若是与今晚的事有所瓜葛,必审出背后主使,一并弄死。
可若真的只是个倒霉的……
更要弄死,哭哭啼啼,吵死!
余青檀悄悄低头,给自己提了个醒。
主上开荤了,以后办事,要多用下半身替主上思虑。
不,是替主上的下半身思虑。
“你晨练?”
她还没从书里脱离出来,完全把那天在饭堂说白凤宸不行的事儿给忘了。
而白凤宸介意的是,沈绰居然敢当众嫌弃,说他不行?
他怎么不会?
他连劈腿都比她劈得妙!
沈绰捧着书,屈了屈膝,木然从白凤宸身边绕了过去。
白凤宸就忽然觉得无聊了。
这牙尖爪利的小东西,难道见了他,不是应该要么作天作地,要么张牙舞爪的吗?
今天居然被忽视了。
他从墙上收了长腿,转身探手,越过沈绰脑瓜顶,就将她手中的书给抢了。
“看什么呢?这么入神?”只看了眼那书的封面,眼光蓦地一厉,一股烟,书就被化了!
“还——我……”沈绰第二个字还没等喊出口,就眼巴巴看着她找了半辈子的书,没了……
她刚刚翻到一个叫“墨重渊”的人,名字只与师父的差一个字,还没看清楚怎么回事,结果那书,就没了!!!
“白!凤!宸——!”
惊天动地的一声咆哮,响彻整个大园子。
所有人听在耳中,都是一哆嗦!
居然有人胆敢如此直吼主上名讳!
沈绰真的炸毛了!
她想跟他拼命!
她想咬死他!
她想把他千刀万剐!
她本就不高的身子,绷成一条直线,两只小手攥得发白,怒目盯着白凤宸!
他好死不死,今天还穿了一身粉得发紫的常服,肩头披了件银狐轻裘,衬在银发之下,整个人只能用“骚、浪、贱”三个字来形容!
这样的沈绰才是有意思的,白凤宸就等着看她如何作天作地。
她作多大,只要他愿意,就都能兜得住。
沈绰瞪他,瞪得两眼仿佛快要沁出血来,可瞪着瞪着,一双眼睛就涌起了一层亮晶晶,水汪汪的东西,之后,两侧俏生生的嘴角往下一扁,一双金豆子,就扑簌簌下来了。
“白凤宸,你到底要怎样!你放过我吧!我既不想攀附你,也不想要你负责,我什么都不要,你放过我吧!”
她居然哇地一声,就哭了,哭得一发不可收拾!
就那么站着哭,也不抹泪,任凭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往下掉。
哭得两肩直抖,哭得心都碎了,哭得隔了几道墙都听得见。
白凤宸当下手脚就乱了,“……,裳儿……”
心里那个记账的小本子,又多了俩字,“哭包”。
他该怎么办?
他从来都没正经哄过女孩子。
本来今日难得闲暇,听说她想逃跑,又被抓了回来,就想来逗她玩,顺便算算账,再研究一下那满天飞的关于“主上他不行”的谣言,结果,怎么只是抢了一本书,就哭成这样?
沈绰啪地打开他伸过来的手,索性蹲在地上,抱着自己哭,那般委屈,无以复加。
金色的堕龙,是师父的徽记,她上一世苦苦想了十年,想知道墨重雪那样神明一样的人物,到底从哪儿来,而她与他决裂后,他和他的人就彻底在白帝洲消失了,他究竟去了哪里?
找来找去,普天之下,只有半卷残破的《太古神荒志》中,记载了关于修罗洲堕龙的传说,可是,那书只有上卷,却无下卷,堕龙和墨重雪到底有什么关系,她完全找不到答案。
如今,好不容易,得了下半卷,又发现了“墨重渊”这个与师父如此相似的名字,本是重新燃起的希望,就又被这个贱人一巴掌给捏成了灰!
沈绰之前伪装的一切强硬,都敌不过此刻的灰心和无可奈何,她连捶白凤宸的力气都没了,就是蹲在地上,缩成一团,使劲儿地哭。
什么天下第一摄政,什么白帝洲之主,不管了,大不了连她一起都拍成灰,还能怎样!
白凤宸也是懵了,蹲下身子,又试探着伸手,一根手指戳戳沈绰的小肩膀。
结果,又被无情甩开。
“裳儿……”
“别喊我!”沈绰吼一声,接着埋头哭。
“裳儿……”
“走开!白凤宸,我这辈子最倒霉的事就是遇见你!”
白凤宸单膝蹲在她面前,摇着头,无可奈何,他怎么知道一本破书能让她哭成这样!
“裳儿,不过是《太古神荒志》而已,大不了孤今日不批折子,亲自讲给你听啊。”
“我不要……嗯?”沈绰的哭声戛然而止,不哭了。
前面,王驾的车撵里,白凤宸对着一只折子,盯着看了有一炷香的功夫,也没动朱批笔。
余青檀在旁边伺候笔墨,大气不敢出。
整个人都扒光了,随身行囊也抖干净了,连丫鬟也被从头到脚都搜了个遍,那被偷走的天机人偶却没有半点踪迹。
沈绰到底把王爷的那个心爱的宝贝藏在哪儿了?
半晌,白凤宸才问:“床呢?”
听说女人都喜欢把好东西藏在床上。
余青檀:“回主上,不要说床,整个闺阁刚刚都拆开过了,院子里也挖地三尺,真的没有。”
白凤宸揉了揉眉心,他讨厌残缺,讨厌不完美,讨厌超出掌控,讨厌这世上还有什么事是他不知道的!
现在沈绰一个人,就把他讨厌的几样都给占了!
可偏偏余青檀这个时候又冒了冒头,“主上,有句话,属下不知当讲不当讲。”
白凤宸也懒得再批什么折子了,烦躁向后倚去,“讲。”
余青檀往前凑了凑,压低声音,“主上,属下疏忽,今日刚刚想起一件重要的事。”
白凤宸凉凉看了他一眼,没说话。
大有办事不力,自领八十大板的意味。
可这事儿,余青檀硬着头皮也要说,“主上,花朝节那晚之后……,咳,沈家小姐忘了喝避子汤……”
他说完,差点将脖子缩进腔子里,就等着挨骂。
这也不能怪他。
他一个爷们,每天忙着伺候另一个爷们,忙得根本不知道女人是什么滋味。
而被他伺候的这位爷们,床榻边清净,从来没有女人。
所以,出了那码子事后,居然没有人第一时间想到避子汤的问题!
白帝洲第一摄政是什么?
是整个白帝洲诸国头顶上的至尊,是所有皇帝中的皇帝,是万王中的王!
长子嫡女要么没有,只要存在,那也是出身尊贵,普天之下的独一份,既不能随便打掉,也不能随便流落在外,更不是随便什么女人都有资格生下来的!
所以,不管这位至尊娶了谁,只要不是正正经经从王府大门抬进去的正妻,这避子汤,就一定要喝!
可现在,晚了!
所以……,那个沈绰,就成了大问题。
“带她来见。”白凤宸的脸色更加难看。
余青檀忙不迭应了,逃命一样滚了出去,传沈绰。
可到了另一头,更头疼。
他喊停队伍,掀开大车帘子,就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。
车上其余的七个,都缩在一个角落里,留出一大块空地,给那三个人打架。
沈绰露着一截腿,身下骑着一个鼻青脸肿的,手里掐着一个满脸是血的,一回头间,披头散发,显然战斗力爆表。
此情此景,香.艳、暴力又血腥、诡异。
余青檀嘴角抽了抽,“四……四小姐,主上召见。”
在这种时候,被白凤宸叫去,俨然刚才这俩姐妹花所说的一切不攻自破。
“下次嘴贱,还揍!”
沈绰倒是颇为受用,当下收手,站起身来,大大方方下车。
可她这英雄,也就当了这一会儿,等再上了白凤宸的车撵,就立刻怂了。
不是怕白凤宸,是没安全感。
身上,除了一件被那两姐妹挣扎时撕得摇摇欲坠的大袍子,连腰带都没了,此时飘飘荡荡,里面就更加凉快……
白凤宸的车撵高大,如一座可以移动的书房,沈绰本就不高,此时就赤着脚,将大袍子把自己裹了裹,站在中央,用力抿着嘴,低着头,眼珠儿滴溜溜转,想着若是出什么情况,该如何应对。
她必是不会让自己再被他欺负了的!
白凤宸端着折子,也没有立刻抬头,静默了好一会儿,才恩赐般地赏了沈绰一眼,可这一眼,就差点把手里的折子掉了。
因为不能束发,防止藏有暗器,所以她头发是散开的,又经过刚才的战斗,此时就凌乱地如乌藻,身前身后胡乱卷曲着。
白色的大布袍子,沾了些许不知道谁的血迹,那领口本就宽大,又被撕破了,就更大,偏偏她还努力在用双臂抱着自己,就更加……
还有那一双赤着的脚,沾了些许泥,踩在马车的地板上,可能因为是凉,或者是紧张,就不小心一只稍稍踩了另一只,上面一只只莹白圆润的脚趾头,颗颗如珍珠一样。
白凤宸:“……”
她这副样子,强烈把他拉回到了花朝节那晚。
他喉间有些干涩,将眼睛勉力挪回到白色织锦做封的折子上,装作若无其事,“你这是怎么了?”
“打架。”沈绰闷声回道。
答得却是爽快。
白凤宸忽然觉得批折子忽然不那么闷了,眉梢几乎不可见地一挑,“旁边的角柜里有衣裳,自己换。”
“哦,谢谢。”沈绰见他不再看自己,又给衣裳穿,总算稍稍放松下来,第一次觉得这人还有救。
“叫主上。”白凤宸也不抬头,纠正她。
“哦,谢主上。”她麻木学了一声,因为脾气比之前稍微缓和了很多,听在白凤宸耳中,竟然多了一丝淡淡的甜味。
他心情又好了一点。
面前,一步之遥,就是衣裳扑簌簌落地的声音。
沈绰背过身去,一面飞快摆弄手里的衣裳往身上裹,一面似小兔子一样警惕回头。
白凤宸始终专注于手里的折子,连眼皮都不曾抬。
沈绰撇撇嘴,倒也算是个君子。
可又怎样?
这世上有些人就是这样,畜生的时候是畜生,君子的时候是君子。
千万不能被表面给骗了!
他那天晚上发狂的时候,可是想要掐死她的!
等她好不容易穿好了,规规矩矩站定,才道:“主上招我来何事?”
白凤宸这才抬头,之后,喉间没忍住,又是一动。
沈绰穿了身银灰色的烧花蟒纹丝缎衣裤,那么宽,那么大,袖子那么长,衣裳到了膝盖,裤腿也拖在地上。
长长的乌黑头发,还是凌乱地散着,就像……
像是刚从他的床上逃出去,穿错了衣裳。
那是余青檀给他备在车撵上,用于夜间替换的寝衣。
她定是又急又慌,随便抓了一身,就赶紧套上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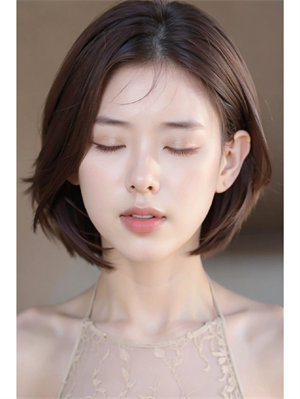 >
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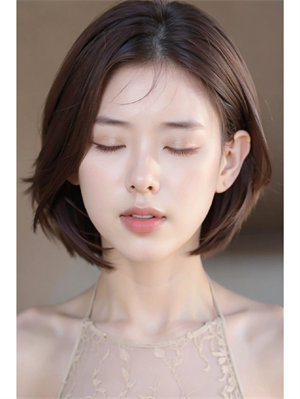
最新评论